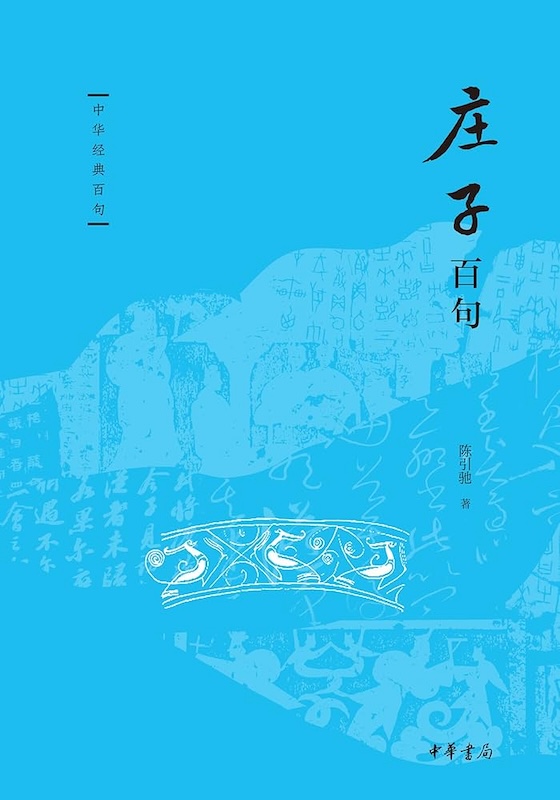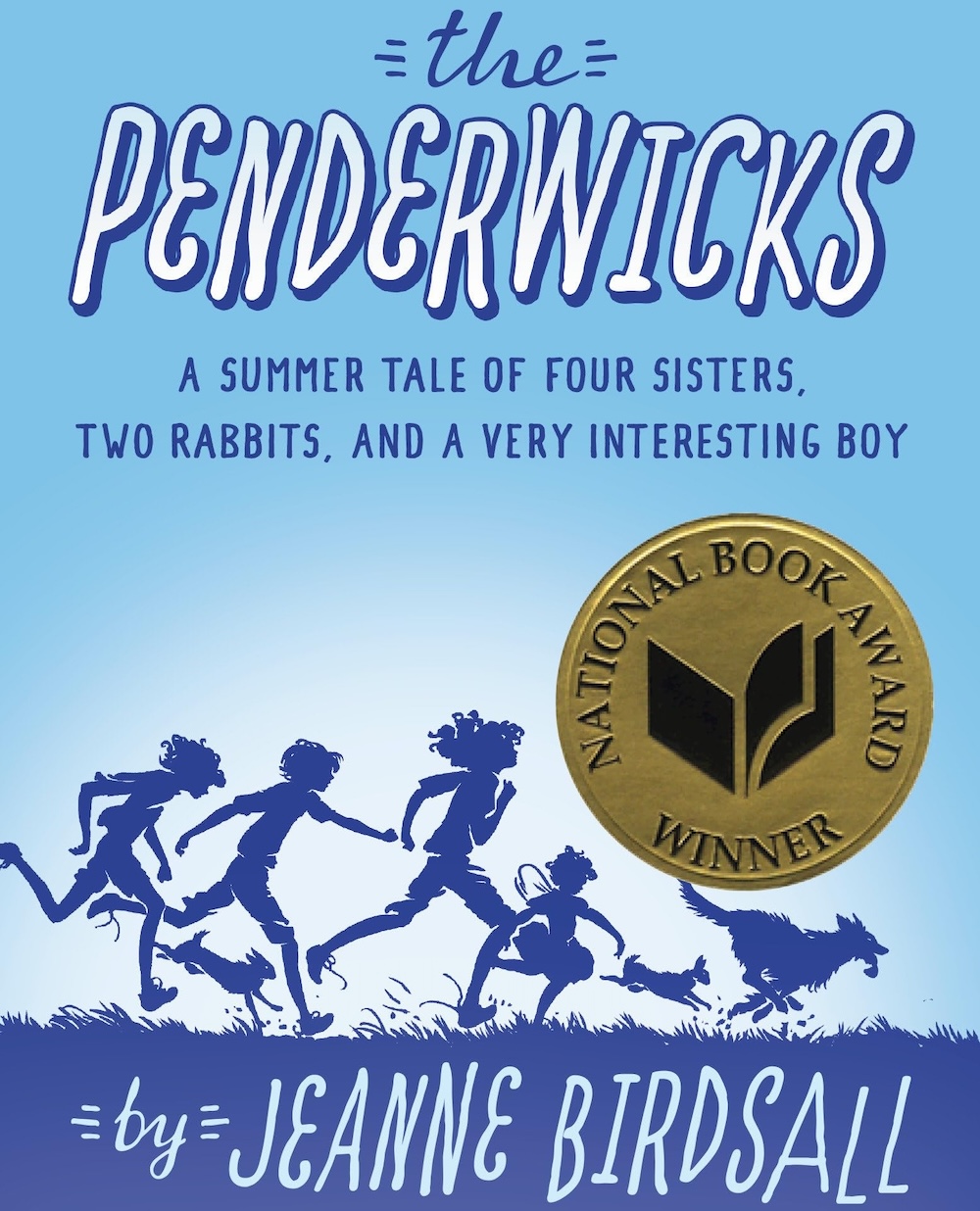继续深入了解陈引驰笔下的庄子及其寓言。
蛮喜欢这本书的,很多文章都可以作为一片议论小短文来欣赏:
《逍遥游》
北冥有鱼,其名为鲲。鲲之大,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,其名为鹏。鹏之背,不知其几千里也;怒而飞,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,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,天池也。齐谐者,志怪者也。谐之言曰:“鹏之徙于南冥也,水击三千里,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,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
’雨果说‘比大陆广阔的是大海,比大海广阔的是天空,而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’。心的世界是至大的,只是一般人们忘却了去展开它而已。在‘则阳’篇中蜗之国的寓言,则是同样的道理,如果站在鲲鹏高飞所在的宇宙立场回顾有限格局中人类的种种行为,不是一样很可笑吗?这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,而是‘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’之后的心胸豁然开朗。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,则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,则芥为之舟,置杯焉则胶,水浅而舟大也。
蓄积深厚才能有腾飞的时候,鲲鹏展翅便是上升’九万里,则风斯在下矣,而后乃今培风‘。人生的成就,多是经历许多努力乃至磨难之后才获得的。然则世间事,得失喜乐总携手而来。鹏程万里,固然人们常常以之为自由的象征;其实,要凭风而起,不也是一种限制或曰不自由么。
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。
鲲鹏展翅,呈现的是空间维度的大境界,这句则提示人们要在时间维度上突破自我的局限。不过人对时间有限的意识,却是随着你日渐失去与他长相守的机缘而增长的,直白些便是:失去越多,就越明白。在这个意义上,人,确实更痛苦。
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,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,定乎内外之分,辩乎荣辱之竟,斯已矣。
自我内在关切了然于胸,然后外在的荣辱都不再会左右自己了。世人非议的,只要确然是合乎自我本性的,‘虽千万人,吾往矣。‘并不退缩;而世人赞誉备至的,也并不飘飘然自喜,因为所作所为并不是为外在的肯定,而是根植于自我的,所以那些都不足以增重。在世俗的世界中,这是一个非常之高的境界;拥有这般境界的人,内心是安宁而高傲的。
鹪鹩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;偃鼠饮河,不过满腹。
‘秋水’中庄子也说‘吾在天地之间,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’,知足常乐。如果一无所有,大概确是很难快乐,但有栖息的一枝,有满腹的饮食之后,拥有越多并不代表一定越快乐。
庖人虽不治庖,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
‘尸祝’嵇康对‘庖人’山涛的鄙夷态度,同样体现了隐士许由对尧的态度。不过庄子中这层在隐世修身和治理天下之间、在道家和儒家扬此抑彼的含义,早已褪尽了。
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,聋者无以与乎锺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?夫知亦有之。
人的五官有缺陷,都会造成很大的麻烦,这些都是无可奈何的事。然而更可难以令人同情的,上不是形质上的缺陷,而是精神上的。所谓视而不见,充耳不闻。
《齐物论》
一受其成形,不亡以待尽。与物相刃相靡,其行尽如驰,而莫之能止,不亦悲乎!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,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,可不哀邪!
身心俱疲,这就是人生的感觉。人都处在这一生命过程中,庄子高出常人处,便是能在精神上超乎其外,返视生命的过程;虽然这一观照给予人的仍是哀恸,甚至更增一层哀恸。
道隐于小成,言隐于荣华。
大道是一个整体,世间万物共处道中,互通互融;如果你要讲一个部分凸显出来,那么或许对这个被凸显的部分是有所成就的,而对整体之道则是一种毁伤。
彼亦一是非,此亦一是非。
彼此、你我都是这个世界整体的一部分,不应该执着各自的是非。
道行之而成,物谓之而然。
人生的道路,看似无形,也是人们行走以后才形成的,并且你不可能沿着任何一条别人踏出的路前行,每一个人都只能自己面对,自己抉择,自己去走。
狙公赋芧,曰:“朝三而莫四。”众狙皆怒。曰:“然则朝四而莫三。”众狙皆悦。
庄子相信世间万物浑然一体,不可强加分判,割裂开来;然而世人往往不能了解这一点,所以偏执一事一物、一个方面,不能有整全的视野,周照全体。也存在一个如何与众人相处的问题,既然多数人都是只顾眼前,急功近利,而缺乏远虑,可以仿效狙公,调整之后皆大欢喜。
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,而大山为小;莫寿乎殇子,而彭祖为夭。
既然事物之间的情状都是相比较而言的,那么站在不同的立场、采取不同的视角,对食物的观照就是不同的,甚至可以与我们通常的印象截然不同。
方其梦也,不知其梦也。梦之中又占其梦焉,觉而后知其梦也。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,而愚者自以为觉,窃窃然知之。
人生一世,是否就是一场大梦呢?而所谓死亡状态是否反倒是觉醒呢?这样想下去,人生是短暂的精神出游,而死亡是回归常态吗?
昔者庄周梦为胡蝶,栩栩然胡蝶也,自喻适志与!不知周也。俄然觉,则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,胡蝶之梦为周与?周与胡蝶,则必有分矣。此之谓物化。
庄子和蝴蝶的分别重要吗?那种快乐自得的感受不是真实的吗?这种感受难道是虚幻的吗?梦,在现实世界中,确实难以把握,但它与我们有着深切的关联,通过它,我们与截然不同的世界有了沟通的隧道,这种沟通是真实的,因为我们享受到了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快乐,我们感觉到自己与世间万物是可以融通的。
《养生主》
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,殆已;已而为知者,殆而已矣。为善无近名,为恶无近刑。
生命是有限的,而知识是无限的,一味地追求知识,愈行愈远,充实的是知识的系统而不是人生的智慧。
安时而处顺,哀乐不能入也。
喜怒不形于色,很大程度上是做给别人看的,在他人的眼中才有意味;哀乐不入于心,则是真正朝向自我的,是对内心世界的呵护。
《人间世》
古之至人,先存诸己,而后存诸人。
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先顾自己,而后才能顾得上别人,不要血气方刚。孔子其实也有类似的段子‘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’,大学的’修齐治平‘也是从自己开始,不是现在通常很容易认为的所谓自私,而是认为人是第一位的, 是最重要的,要成就任何事业,必须首先着力在人本身,这才不是本末倒置,才不会最后落空。孔子又说’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‘。
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
唐代朱庆余在科举考试前,写了一首‘今试上张水部’投赠水部郎中张籍‘洞房昨夜停红烛,待晓堂前拜舅姑。妆罢低声问夫婿,画眉深浅入时无?’张籍当然也听懂了他的弦外音,回赠‘越女新妆出镜心,自知明艳更沉吟。齐纨未足时人贵,一曲菱歌敌万金。‘所有人类表达中的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,都是用心才能听到的。
绝迹易,无行地难。
比喻人之行世,明代释德清解释道‘逃人绝世尚易,独有涉世无心,不着形迹为难’。达到这样的境地,除了飞行如何可能呢?那就是依顺世道,深通事理,内无心而外无为,如庖丁解牛一般,以‘无厚’之刃入‘有间’的牛之骨架,游刃有余,十九年刀刃未曾损伤。
为人使,易以伪;为天使,难以伪。
以人之情欲为动力的所作所为,往往是不合天道的,是‘伪’的;相反以循天道而来的作为则不是伪的,是真的。所以庄子选择按照自己天性的喜好,过自己的生活,他相信自己的生活是真实的,自己的心是真诚的。
朝受命而夕饮冰。
来源于叶公子高的故事,叶公是一个将世俗责任看得很重的人,是一个忠心国事的人。近代的梁启超与叶公产生了共鸣,他为近代中国的困境和问题焦虑不已,迫切期望能完成拯救天下的使命,故而将自己的室名定位‘饮冰室’,文集成以‘饮冰室‘为名。
其作始也简,其将毕也必巨。
庄子从负面的意义上以为,事情从初开始的时候是微小的,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就变成大祸了。正确的应对策略就是要能见微知著,要防微杜渐,要防患于未然。
意有所至,而爱有所亡。
庄子的原意是要讲伴君如伴虎的道理。喜爱固然应该表达出来,藏着不露,不是合适的做法,但也不能过度。过度的爱,会导致被爱之人持宠而娇,行为无端。
山木自寇也,膏火自煎也。桂可食,故伐之;漆可用,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,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
庄子警告人们,不要以为通常所谓有用、无用是永远有效的,不能以此为标准来估价所有事物。庄子站在生命本位的立场上,提出了与世俗所谓有用、无用不同的判断。这有理论上的原因,很大程度上也与那个生命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中的时世有关。
《德充符》
自其异者视之,肝胆楚越也;自其同者视之,万物皆一也。
庄子对于人的主体地位,有强烈的自觉意识。苏轼与友人泛舟赤壁,客人感叹美好月光流逝,生命短暂;苏轼的劝慰之言即脱胎换骨于庄子:‘自其变者而观之,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;自其不变者而观之,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’从变的角度来看,一起都在变化,天地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变化,否则如何有沧海桑田?从不变的角度来看,则我们与万物一样,都没有终结,我们不是都存在于天地之间么?
人莫鉴于流水,而鉴于止水。
孔子说‘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’;老子说‘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攻坚强者,莫之能胜。’庄子管子关注到静止的水而不是流动的水,他注意到只有静止的水才能映照影像,而流动的水波光荡漾,一切都在移动,无从把握。这是一个日常经验,然而具有深切的意味:只有如同静水那样波澜不兴、略无偏执的心灵,才能了悟世间种种情状。
鉴明则尘垢不止,止则不明也。久与贤人处,则无过。
止做存讲。庄子在镜子的比喻中谈到了尘垢,如果要镜子明澈,就得不让他沾染灰尘,有灰尘则不能明晰映照了。后世不管是神秀的‘深入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,莫是染尘埃。’还是李世民的‘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。’
德有所长,而形有所忘,人不忘其所忘,而忘其所不忘,此谓诚忘。
人的形貌是天生的,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很多改变的可能。然而人的内在修养,自己却可以做很大的主。‘德’,既是‘德性’之义,同时‘德’者‘得’也,是指人内在地得自于‘道’的那部分。得自‘道’的‘德’,是真正应该把握的,应该牢记不忘的。外在的那些东西,倒是不该或者干脆就不必记住的。
《大宗师》
其耆欲深者,其天机浅。
天机,乃是合乎天道的自然本性;在庄子看来,它与人的种种欲望构成尖锐对立。苏轼喜好书画,碰到喜欢的总会收一些,但如果被人取去,也不当回事,’譬之烟云之过眼,百鸟之感耳‘。他非常清楚:‘君子可以寓意于物,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寓意于物,虽微物足以为乐,虽尤物不足以为病;留意于物,则微物足以为病,虽尤物不足以为乐。’人都有欲望,对欲望,如同苏轼之于物,不可留意‘,也就是不可’深‘。这叫做保有‘天机’。
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。
“相濡以沫”,在今天无疑具有正面的意义。庄子对此,并无异议;他能细致观察身处危险境地的鱼儿们的动作和情谊,简洁贴切地将它们传达出来,没有悲天悯人的同情心,是难以想象的。
然而,庄子不同常人之处,或许正在平常人仅抱着一种想法的时候,他却能有异乎寻常的感受。这种感受源于他超乎时流的立场。庄子从世界万物的本然状态考虑:鱼就应该生活在水中,在水中它们才能悠游自在;脱离了水,就是脱离了生命的自然状态,就是一种生存状态的扭曲。因而,鱼儿在陆地上,无论怎样互相支持,努力求生,终究是可悲的。
回到人世,《庄子•知北游》引述了老子的话,这番话原见于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:“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。”仁义,在儒家的思想世界中,具有无可置疑的正面价值,但是老、庄等道家则尖锐指出:仁义不过是丧失了真正道德之后的次一等境界,当真正的道德尚存世间的时代,仁义是没有必要的,就如同鱼在水中的时候,相濡以沫的相互关切是没有必要的一样。
仁义之类正面价值是不需要的,那么善恶的分别也就不必要。所以庄子接着就说:“与其誉尧而非桀,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”圣人尧和暴君桀之间,就不必加以轩轾了,应该忘却两者,而同归于道。
归于道,则如鱼回归水,“鱼相忘乎江湖,人相忘乎道术”。
《应帝王》
南海之帝为儵,北海之帝为忽,中央之帝为浑沌。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,浑沌待之甚善。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,曰:“人皆有七窍,以视听食息,此独无有,尝试凿之。”日凿一窍,七日而浑沌死。
浑沌的寓言,充分表达了庄子的许多基本思想。
首先,浑沌形象体现了整全一体的意旨,它不是分裂的,不是支离破碎的,这是庄子有关世界原初状态的象喻。
其次,“倏”、“忽”的意思是迅速快捷,暗示着时光的流逝;在时间的维度中,世界流变不居,也是庄子等古代哲人一再思考的问题。
再次,随着时光流逝,整全的世界发生了分裂,这一分裂,宣示了本初状态的结束,宣示了浑沌本性的死亡;这七天,不是创造世界的七天,而是毁灭的七天。
复次,庄子对以分析的态度面对世界持批评立场——无论这种分而析之,是倏、忽二位这样“日凿一窍”的行为,还是如惠施、公孙龙等名家知性上的精神活动;相反地,应该以与万物会通的态度,直面世间万物的缤纷多彩。
最后,以“人皆有七窍”的一般状况,要求一切事物,并且不顾万物各自的品性,将单一面貌强加于人,也是庄子所不能接受的。比如庄子就曾批评惠施以能盛水作为衡量葫芦的唯一标准,那超过一般尺度的大葫芦,何以不凭之浮游江湖之上呢?
如果要选一个最能代表庄子观念的形象,我很可能投“浑沌”一票;如同对老子,我会投“水”一票。
《骈拇》
小惑易方,大惑易性。
‘小惑‘迷失的是方向,’大惑‘迷失的这是根本,是本性。林中归鸟认得还巢的路,是不犯小惑,而鸟为食亡这是陷于大惑。
能无’大惑‘,得有过人的智慧。陶渊明可以算一个。他也曾出仕,奔走宦途。然而, 他最终’实迷途其未远,觉今是而昨非‘,醒悟到自己’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‘,在本性上是喜好自然而不是喧嚣的官场,于是毅然抽身而退,在田园中寻得安身立命之所。陶渊明真是’大惑易性‘的方面。
人世间有许多这样的情形:一个并无世俗意义上辉煌成功的人,或许是真正把握了自己的本心而无大惑的人;而一个事事算计的极清楚,似乎步步走得都很聪明的人,或许正身困大惑之中而不觉,大步走在背离自己本来真性的大路上。
小人则以身殉利,士则以身殉名,大夫则以身殉家,圣人则以身殉天下。故此数子者,事业不同,名声异号,其于伤性以身为殉,一也。
在现世,庄子最关切的是人的生命,是能保守自己的天性,是可以从容地安度天年,不夭折也不妄图延续永久。
圣人对为天下而丧生,有着清楚的自我意识,这是他主观抉择的结果,与小人之不由自主奔忙利益招致丧亡有所不同。孔子说过: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生以成仁。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孟子也表达过:“生,亦我所欲也,义,亦我所欲也;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(《孟子•告子上》)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气概。
然而,庄子要问:这就对了吗?无论为了什么,最终都是丧失了现世中最可宝贵的生命,圣人与小人在“伤性以身为确”一点上,不是一样的吗?
天下尽殉也。彼其所殉仁义也,则俗谓之君子;其所殉货财也,则俗谓之小人。其殉一也,则有君子焉,有小人焉。
既然都是‘伤性以身为殉’,犯的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,那么何必轩轾其间呢?庄子给出的例子是伯夷和盗跖。伯夷大约不会认盗跖为同道,但估计盗跖会引伯夷为同志,因为它也是讲‘圣’‘勇’‘义’‘智’‘仁’的。
《胠箧》
盗跖之徒问于跖曰:“盗亦有道乎?”跖曰:“何适而无有道邪?夫妄意室中之藏,圣也;入先,勇也;出后,义也;知可否,知也;分均,仁也。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,天下未之有也。”由是观之,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,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;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,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。
盗亦有道,那一般所谓的正面的价值,真的始终具有正面的用处吗?庄子对‘圣人之道’提出另一侧面的观照,坏人可能用了好玩意儿,好玩意儿帮了坏人的忙。庄子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,人们为了防盗,往往将箱子柜子锁牢捆紧,但来了大盗,连锅端的主,他倒唯恐你锁得不牢捆的不紧。正因为原来弄得好,才造成更坏的后果。庄子进一步指出,因为天下好人是少数,坏人是多数,那么坏人利用‘圣人之道’的概率,要大大超过好人,故而整体而言,‘圣人之道’对天下是利少弊多的。这里,透露出庄子对人的悲观,与儒家比如讲‘性善’的孟子截然有异。
窃钩者诛,窃国者为诸侯,诸侯之门,而仁义存焉。
盗有小盗,有大盗。‘圣知之法’成了窃国者最有效的工具。庄子亲见了田氏代齐。‘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’,权利掌控了道义,道义与权利合媾一处了。
《在宥》
君子不得已而临邪天下,莫若无为。
庄子头脑里,最好不要去担当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角色。如果不得不出来做事,就‘无为’。这’无为‘不是说一切都放下,什么也不干的意思,而是指依循这世间事物自然的变化消长,而不强为、不妄为。拔苗助长就是妄为、强为。道家在政治上一贯主张’无为‘,《老子》五千言便反复致意于此。奉行’无为‘的政治原则,其最高的境界乃是下面被治理,被统治者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;敬爱而赞美统治者的,已经等而下之;至于畏惧或轻侮统治者的,更不足论了。(《老子》第十七章:太上,下不知有之。其次,亲而誉之。其次,畏之。其次,侮之。)
《天地》
有机械者必有机事,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
庄子借了子贡劝老人用机器抽水的故事,来说使用机械便会生出机心,使得本性就此扭曲。庄子宁可劳力,而不愿劳心。
《天道》
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。
如今的朴素理解做简单平淡就是美,但在古代,朴素即保持了原本性状、未经妆点改易。在庄子心中,至高的不是美,而是保守本性的纯真,美是本性之真的结果。
君之所读者,古人之糟魄已夫!
这句话好像挺适合现在的AI的。庄子对言语表达精微意义的能力,一直持怀疑态度。他在《秋水》篇中,已经明确表示了言语之类对’道‘是无能为力的,只有对现实世界中属于’物之粗‘的部分,言语才有效,’物之精‘那一部分,主要靠意想(“可以意致”)。
庄子借用了齐桓公和轮扁之间的对话,来说语言文字的无用,或者能力有限。就算是‘物之精’的技艺部分,虽然奥妙,但还不是‘道’,他面对的还是‘物’的世界。文惠君从庖丁解牛中领悟了养生之道,不知道齐桓公领悟到了什么?
现阶段的大语言模型AI,不也是如此么。伟大的自然天道造就人,人造就AI,我们还是要相信自然天道,相信人。
《天运》
西施病心而矉其里,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,归亦捧心而矉其里。其里之富人见之,坚闭门而不出;贫人见之,挈妻子而去之走。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。
《天道》‘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‘,保持了天然本性就是美,由此,就可以真正理解东施效颦故事的意思了。
西施之颦之所以美,其实不在她是美人因而一切皆美,而是因其“病心”,这是出自真“心”的。而东施效颦之所以丑,也不是因为她原本就丑,而是她并未“病心”,故而其颦非出本心,纯属模拟造作。东施一意追求世俗所认同的美,矫揉伪饰,导致丧失了自己的本真。可以设想,如果西施没有“病心”而“颦”,恐怕庄子也会笑话美人的吧。
这种违逆自己本性,而盲目认同并追逐世间一般价值的作为,是庄子一贯讥讽的。那个有名的“邯郸学步”的故事,也不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:燕国寿陵地方的一位年轻人,到赵国的邯郸去学那里的步态,结果没学好新的,原来走路的步法也忘了,只好爬回老家去。(《秋水》:“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邮郸与?未得国能,又失其故行矣,直匍匐而归耳。”)这不也是失其本来固有的结果吗?
其实,“颦”不过是形迹,效颦是东施错误的外在表现,如果要以庄子口气来批评的话,那该是“东施效心”。
夫水行莫如用舟,而陆行莫如用车。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,则没世不行寻常。
孔子希望师法先王,克己复礼,重整当时礼崩乐坏的世态。而在庄子看来,过去的世界,即使是黄金时代,也与现在相隔甚远,犹如水、陆之不同,如果要将周礼实行于当今孔子的故乡鲁国,结果大约也就是推舟于陆、行车水中了。庄子提出,所有治世的礼义法度,都应该‘应时而变’,与时俱进。
似乎在这里,庄子只反孔子,不反周公。
《刻意》
形劳而不休则弊,精用而不已则劳,劳则竭。
道家高度重视生命的保养,而生命的基本层面可以分为形与神。在形、神两方面,都不应该过于劳苦。古代例如贾岛为‘独行潭底影,数息树边身’,‘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’的苦吟诗人终究不能是主流。
《缮性》
古之所谓得志者,非轩冕之谓也,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。今之所谓得志者,轩冕之谓也。轩冕在身,非性命也,物之傥来,寄者也。
世人看重的地位权势,庄子以为是偶然而来,也将偶然而去。权势地位都不是性命本来固有的,是偶然而来,暂时寄于我身而已。
庄子倾心的是真正的纯粹的快乐,这种快乐根植于生命本身,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。能保全生命的本然,乃是最值得快乐的。这种快乐不会因为世俗所认可的种种外在价值而增减,这才是庄子所认可的‘得志’。
丧己于物,失性于俗者,谓之倒置之民。
‘物’是相对于‘我’而言的,‘俗’则是对立与’真‘;丧失了自我,丧失了本真,便是颠倒。在外物和自我之间把持不住重心所在,一味追逐外在的东西,而不能反躬自省,进而自珍,此类情况古今可谓多矣。‘人为财死, 鸟为食亡’。
世间流俗的观念对人们的左右力量,亦是非常之强大。尤其现代社会,资讯的发达和充分流通,使得一般观念之流行远远超越以往。问题不在差异,现代世界前所未有的丰富性,提供了欣赏差异的机会;问题是’见异思迁‘,看到差异以后,不顾自己的情况,企慕追攀,丧失了自己的本真。
《秋水》
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,拘于虚也;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,笃于时也;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,束于教也。
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导致了‘小知不及大知’,而一个识见寡陋偏执的人不能明道,是受到了他所接受的知识教养的限制。
《庄子》提出的警示是要知道知识的有限性,在照察一隅的同时,明了他对其他的方面或许存在盲视,尤其当你固执于自己的照察之时。教养具有更强烈的文化特性,而任何文化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。
精粗者,期于有形者也;无形者,数之所不能分也;不可围者,数之所不能穷也。可以言论者,物之粗也;可以意致者,物之精也;言之所不能论,意之所不能察致者,不期精粗焉。
庄子对世上的事物有一个分析,一类是所谓‘有形’的,一类则是‘无形’的。无形的一类,正是不能精细把握的,无法用言语描述;至于有形的一类,进一步分为精、粗两类,粗的部分可以言论,精的部分可以意致。
而言语和知性能抵达的边际即是‘物’,‘道’与‘物’相对,‘道无始终,物有死生’。‘物’是这个世界中的现象,有生有灭;‘道’是永恒性,超越生灭之外。于是我们了解到庄子的基本观点乃是:言语对于物质世界的现象乃至条理,是可以把握和传达的,而对于‘道’这无能为力。
以道观之,物无贵贱;以物观之,自贵而相贱。
继续讲‘道’与‘物’的鸿沟。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,就有点’道不同,不相为谋‘的味道。
梁丽可以冲城,而不可以窒穴,言殊器也;骐骥骅骝,一日而驰千里,捕鼠不如狸狌,言殊技也;鸱鸺夜撮蚤,察毫末,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,言殊性也。
世间万物,个性不同,平等对待,依循其性,各尽其能。此乃庄子面对纷纭事物的基本立场。
知道者必达于理,达于理者必明于权,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。
论语中‘邦无道则愚’的宁武子,想必是知道者。这里的‘权’,权变,不是当没有原则的墙头草,而是要在通达‘道’与‘理’的前提下,审时度势,有所变通,这是一个原则性与灵活性很好结合的高境界。
无以人灭天,无以故灭命,无以得殉名。
三个‘无以’,就是要做一个合乎天道的自然的人,保守人的本性,保全本来自我。
庄子钓于濮水,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,曰:“愿以境内累矣!”庄子持竿不顾,曰:“吾闻楚有神龟,死已三千岁矣,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。此龟者,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,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?”二大夫曰:“宁生而曳尾涂中。”庄子曰:“往矣!吾将曳尾于涂中。”
庄子在《人间世》里说‘方今之时,仅免刑焉’,汉末的诸葛亮也说‘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’。
惠子相梁,庄子往见之。或谓惠子曰:“庄子来,欲代子相。”于是惠子恐,搜于国中三日三夜。庄子往见之,曰:“南方有鸟,其名为鵷鶵,子知之乎?夫鵷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,非梧桐不止,非练实不食,非醴泉不饮。于是鸱得腐鼠,鵷鶵过之,仰而视之曰:‘吓!’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?”
苏轼被贬黄州,做《卜算子》: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此时的他正处在人生的低谷,仍然不肯乃至不屑于同乎流俗。远翔中的鵷鶵更不必说了。
人的一生,有时候不能只是守着眼前的利益,要知道放弃,仰头看天上飞过的鵷鶵,目送归鸿,望着它消逝在远方的天际,想象那里有怎样的风景。
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。庄子曰:“儵鱼出游从容,是鱼乐也。”惠子曰: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”庄子曰:“子非我,安知我不知鱼之乐?”惠子曰:“我非子,固不知子矣;子固非鱼也,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。”庄子曰:“请循其本。子曰‘汝安知鱼乐’云者,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,我知之濠上也。”
看似庄子在混淆逻辑,其实世间不仅是现实,世间不仅有逻辑。庄子展示的是一个通达天地自然,与万物沟通无碍的心灵。鱼游水中,我游梁上,同样的自在率意,鱼我双方是融通的。鱼乐其实是我乐的映射;我乐,故而鱼亦当乐。杜甫有诗云: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,一哀一乐而已。
庄子坚持自己的观感,反对的正是惠子的细琐分析。这个世界有时候是不能分拆开来加以了解的,’七宝楼台,眩人眼目,碎拆下来不成片段‘。
《达生》
养形必先之以物,物有馀而形不养者有之矣;有生必先无离形,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。
庄子对于生命的观念,是依顺自然,尽其天年。所以中途夭折固然不好,妄图无限延续生命的长度,也是不恰当的。在这个意义上,如果仅仅是保有了身体的存在,并不能说你的生命依然在延续,比如,精神丧亡、行尸走肉的情况就是如此。这是‘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’的一层意思。稍加引申,或许可以说,‘养生’要养的是真正的生命活力,此‘生’要具有内在的价值;如其活力和价值已失,那么虽然‘形’还在,而‘生’已亡了:“有的人活着,他已经死了”。
醉者之坠车,虽疾不死。骨节与人同,而犯害与人异,其神全也,乘亦不知也,坠亦不知也,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胷中,是故遻物而不慑。
‘无知者无畏’,心以为险则险,心以为安则安。不过现在‘无知者无畏’基本做负面的理解了。
仲尼适楚,出于林中,见痀偻者承蜩,犹掇之也。仲尼曰:“子巧乎?有道邪?”曰:“我有道也。五六月累丸,二而不坠,则失者锱铢;累三而不坠,则失者十一;累五而不坠,犹掇之也。吾处身也若厥株拘,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,虽天地之大,万物之多,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不侧,不以万物易蜩之翼,何为而不得!”孔子顾谓弟子曰: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,其痀偻丈人之谓乎!”
要想有所成就,不分散注意力(用志不分),精神凝定专注(乃凝于神),是关键的一个环节。
以瓦注者巧,以钩注者惮,以黄金注者殙。其巧一也,而有所矜,则重外也。凡外重者内拙。
庄子讲的是赌博,随着赌注的增加,心里的压力、紧张感愈来愈重,原先的潇洒变成了害怕乃至昏聩。人们的智巧能力是一样的,但如果特别在意实际的结果,反而不能充分发挥出来。‘外重者内拙’,专心外在事物的人,内心会逐渐沉没、枯寂下去。不如回返内心,倾听心底的声音,重获心的灵明。
《山木》
处夫材与不材之间。
‘材与不材之间’,一般的感觉,有混世的味道。但危殆的时世,如果聪明地生存是一个难题。或许聪明的表现还得是愚蠢,更准确地说是装傻。孔子曾称道卫国的宁武子:国家昌明有道的时候,他很智慧;国家昏昧无道的时候,他便很蠢。他的智慧可以学得,他的愚蠢却学不来啊。(《论語•公冶长》:“邦有道则知,邦无道则愚。其知可及也,其惑不可反也。”)
宁武子倒真是一个善“处乎材与不材之间”的人物。
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,望之而不见其崖,愈往而不知其所穷。送君者皆自崖而反,君自此远矣。
‘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,惟见长江天际流’,李白一直站在岸边,遥望朋友的远帆,直到他融入江天之际,透露出深深的眷恋情谊;而《庄子》总的修道者,因道行日深,同道当然越来越少,日渐孑然,送者纷纷散去即喻指此也。
以利合者,迫穷祸患害相弃也;以天属者,迫穷祸患害相收也。
因利益而聚,往往也因利益而散。而以天性自然结合在一起,但艰难困苦来临的时候,人们往往互相拥抱,互相支持。如果哪一天,‘天属’浸透了‘市道’,也就是乱世了。
君子之交淡若水,小人之交甘若醴。
君子、小人,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对举的两类人。
君子惺惺相惜,相互之间一望而知,所谓“相视而笑,莫逆于心 (大宗师》)。只是他们之同的关系,建立在共同的信念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欣赏基础上,因为有本质的契合,无需过多的外在表现。或许,许多时日并无往还,但他们的内心还是认同对方的,细水长流,重逢时依旧未见隔阂。
与君子之间的静水流深相形相对的,是小人之间看似浓烈的热络,像浓浓的甜酒。生活中缺乏真正的甘美,于是企望甜腻的口味;真正尝过甜美的人,反能懂得平淡的真意。
君子、小人之间的对比,真正的君子都能分辨。《论语•为政》有“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”之说,是说君子的态度比较周遍、周正,小人则朋比为党。朋比为党,就是腻歪地搅合在一起:而他们之间因为没有真正的心灵契合,没有道义的共识和实践,因而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闹分裂。
庄子在上引句的后面,接着有一句:“无故以合者,则无故以离。”这“故”,用得很吃紧,小人之同无缘无散地合,无缘无故地分,这正是与君子间交谊的大不同处。
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。
总是观照于污浊的水,对源头清泉也丧忘殆尽。这暗喻着人的本性的丧失,在污浊的世界上,见怪不怪,习非成是。
《田子方》
中国之君子,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。
这是《庄子》里批评孔子的话,指出儒家的错误即在讲外在的礼义认作根本,轻略了人心、人性的根本。
庄子的人性观念,突出的是本来自然的一面,认为它基本是淡漠的;而对灵动的人心,庄子则有非常深细的观察,提出人心难以了解,它比山川还要曲折险峻,比了解上天还难。于是安顿内心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哀莫大于心死,而人死亦次之。
这是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言语。
身体的死亡,固然很是令人悲哀,但一则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,庄子主张安时处顺,平静接受;况且庄子虽然重视人的生命,但在他心中,形体的保养是次要的。而“心”,则代表着人的精神,当心死的时候,即使形体尚存,那也只是行尸走肉。
心死,意味着人丧失了对自我的肯定,丧失了自我的自觉意识,丧失了生意生趣,意味着人放弃了自己在世上的生活,意味着一切都不可也不能为了。
值得提出的是,这里的“心死”与庄子喜欢说的“心如死灰”(《齐物论》)的状态,并不是一回事。“心如死灰”是一种极而言之的形容,指排除了一切纷杂的欲念和多余的知识,臻于虚空平静之极致的状态;这时,你的内心并没有死寂,而是准备着迎受大道的光临。《大宗师》篇中孔子与颜回谈论“坐忘”,“坐忘”就是抛开形体,泯灭聪明,而后与大道相合(“堕肢体,點聪明,离形去知,同于大通”)。
“心如死灰”的后面,不是一无所有,而是有一个更大的与天地宇宙会通的期待和奇迹:
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
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
《知北游》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而不议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
庄子对于喋喋不休的言说,始终有怀疑。他真正喜欢的,是直面宇宙天地,与万物并生共育,而不是将它们作为对象加以描写、分析。‘不言’‘不议’‘不说’,即此之谓。
古代的哲人们,面对世界万物,多能体会到它的庄严,体会到它的美,它的自然次序。孔子也曾感概‘天何言哉!四时行焉。’
后世的人类,精神发展到自我中心,毫无敬畏,仅存功利的利用之意,以致讲‘不言’‘不议’‘不说’,径自当作‘不能言’‘不能议’‘不能说’,甚至干脆认为外在世界是没有升级的,可以任我宰制。我们需要谦卑地谛听自然的声音,体会宇宙的消息。
山林与!皋壤与!使我欣欣然而乐与!乐未毕也,哀又继之。哀乐之来,吾不能御,其去弗能止。悲夫!世人直为物逆旅耳!
在自然山林和平川的环境中,愉悦情绪油然而生,然而快乐与哀伤形影相随。哀乐的来去,不能遏制,人成为它们的寄寓之所。
这段文字可谓‘兰亭集序’的模本。不过后者更明确的给出了‘哀’的来由;‘死生亦大矣’,《兰亭集序》的引语即出自《庄子.德充符》,这也是庄子反复且深切考虑的问题。
《庚桑楚》
知止乎其所不能知,至矣。
古希腊有位哲学家,他的学生问他:“老师,您的知识比我们多许多倍,您回答问题又往往很正确,可您为什么总怀疑自己的答案呢?”哲学家用手指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,回答说:“大圆圈的面积代表我的知识,小圆圈的面积代表你们的知识;两个圆圈的外面,代表无知的部分。我的知识,自然比你们的多,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的长,那我接触到的无知的范围自然也比你们的广。这便是我为何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啊。”
庄子以为,真正的智慧是在能驻足和不能驻足的边界止步。‘对不可言说的,我们应该保持沉默。’
《徐无鬼》
以贤临人,未有得人者也;以贤下人,未有不得人者也。
庄子借管仲鲍叔牙和隰朋的故事,留下了关于贤能人士的观察标准:身处高位优势的人,更应该放下身段,谦卑恭敬,容得下人,具有同情心。
《外物》
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。夫地非不广且大也,人之所用容足耳。然则厕足而垫之,致黄泉,人尚有用乎?
除了跟惠子讨论大葫芦的有用无用外,庄子还列举了这个例子,来说明有用和无用是相对而言的,如果你只要所谓有用,抛弃所谓无用,最后有用也是不能成立的。
老子也曾论‘有’与‘无’的关系,第十一章中提及制作一个器皿,不能仅仅注重她有形的部分,器皿之称其为有用的东西,还在于它所包含的空的部分;窗户的道理也一样,窗框固然有形而有用,但窗更重要的部分在他敞开的部分,这里才能容受空气,容受阳光。
世界的真实情况,在于这样的有无之间。
荃者所以在鱼,得鱼而忘荃;蹄者所以在兔,得兔而忘蹄;言者所以在意,得意而忘言。
庄子对人们的言说,怀有深切的不信任。虽然但是,虽然言语的传达不能充分传达出真意,但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途径,只要不执着于这个手段,心中清楚追求的根本目标是‘意’而不是‘言’,即‘言者所以在意’,因‘言’而窥‘道’,就是了。而在‘得意’之后,即可放开言语(忘言),不要死于句下,不要纠缠于手段。试想:你过河走的是桥,已然过河,但还在桥头徘徊,你算真正过河了吗?
《寓言》
寓言十九,重言十七,卮言日出,和以天倪。寓言十九,藉外论之。亲父不为其子媒。亲父誉之,不若非其父者也;非吾罪也,人之罪也。与己同则应,不与己同则反,同于己为是之,异于己为非之。
庄子的开创了寓言,但庄子的寓言是‘籍外论之’,‘意在此而言寄于彼’,也就是转借别的话头来讲论自己要表达的意思。因为庄子的言谈,出于种种不那么恰当的世俗理解,往往无法为人接受,所以庄子要用寓言来表达:这世上一塌糊涂,没法正正经经地说话。《天下》:“以天下为沉浊,不可与庄语”。
《让王》
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,世必笑之。是何也?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。
庄子还是在告诫人们要重视生命,不要像以贵重的宝珠来弹射鸟雀一样,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轻易付出,去追求那些不值得的荣华富贵、名声地位。多少人放弃了自己已拥有的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,只是为了世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。
身在江海之上,心居乎魏阙之下。
唐代‘随驾隐士’卢藏用,随天子往返长安洛阳之际往来终南、少室二山,最后终得武则天征召。一次与好友道士司马承祯聊天,“藏用指终南山,谓之曰‘此中大有佳处,何必在远。’承祯徐答曰’以仆所观,乃仕宦捷径耳。‘”
贬义之外,庄子对假隐士还是宽贷的,如果假隐士不能克制自己的世俗欲望,那就顺从算了;否则勉强克制,只会二次受伤,那就活不久了…生命还是最重要的。
《盗跖》
好面誉人者,亦好背而毁之。
当面赞誉,在过去是令人尴尬的事,因为传统是讲究谦逊的,如果一个人敢于当面大肆叫好,总值得疑虑。
不仅当面称誉其心可疑,而且既然可以不合常规地当面称誉,也有很大的可能背后诋毁,无论称誉还是诋毁,反正都不是出其真意,而是视利益需要而定的。既然可以翻掌成云,自然也可以覆手为雨。
人上寿百岁,中寿八十,下寿六十,除病瘦、死丧、忧患,其中开口而笑者,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。
庄子对人生基本持悲观的看法。人们往往期望好的状态,期望愉悦的心情,于是排除那些不顺心的时日,然后排除了以后,真相是:高兴的时候实在不多,开口而笑者,一月中不过四五日,算起来一个星期一天吧…
天与地无穷,人死者有时,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,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。不能说其志意,养其寿命者,皆非通道者也。
生命有限,解息而过。骐骥过隙这个意象,在庄子中也是屡见不鲜的,《知北游》中亦有“人生天地之间,若白驹之过隙,忽然两已”之语。
面对这个事实,我们该如何把握自己的一生。从总体上说,庄于主张平静地度过自然的一生,不过,在这个过程中,也应该尽量称心快意,何必委屈自己呢?
不过,这里有一个分寸,庄子并不是在主张及时行乐。及时行乐,因为知道一切都会过去,所以竭力抓住眼前可能的快乐,有一种绝望的表情,有一点颓废的气味,还有一点嚣张的派头。庄子的快乐是安静的,是恬然的,是濠梁之上观鱼,而物我同一畅怀。
悦其心志,是滋养生命,而不是放纵生命。
《渔父》
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,举足愈数而迹愈多,走愈疾而影不离身,自以为尚迟,疾走不休,绝力而死。不知处阴以休影,处静以息迹,愚亦甚矣!
庄子是一个敏感的人,敏感的人对光影一定会痴迷。庄子多次谈及形与影的关系,比如《齐物论》最后庄生梦蝶一节的前面,就有关于影子的一番对话。影子说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依傍而行。
此处逃影的情节似乎更有意趣。影随形动,形影不离,要消除痕迹,只有从根源处着手,那就是“处阴以休影”,自我不那么显耀,影迹自然也就消逝。移说现世,即应虚己而游。
人如能虚己而遨游于世,谁还能对他造成伤害呢?虚己就不奔竞于外;虚己就不徒耗形神;虚己就合体于自然大道。
真者,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。故强哭者虽悲不哀,强怒者虽严不威,强亲者虽笑不和。真悲无声而哀,真怒未发而威,真亲未笑而和。
道家非常基本的一个祁向,就是‘真’。某种程度上与儒家所着力突出的‘善’,可以相互对照。所谓‘真’,就是本真,就是保守原初的情态,不扭曲,不造作,一任率真。发自真情的喜怒哀乐,并不一定在意外在表现的形式,关键在内心的实质。
《庄子》接下来还说到:饮酒以快乐为关键,居丧以哀伤为关键。故而饮酒意在追求快乐,所以不必讲究酒具如何;居丧以悲伤为要,所以不必讲究礼法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母亲去世后,不守礼法,‘然后临诀,直言穷矣,举声一号,因又吐血数升,毁瘠骨立,殆致灭性。’,可谓实践‘真’的典型。
《列御寇》
吾以天地为棺椁,以日月为连璧,星辰为珠玑,万物为赍送。吾葬具岂不备邪?
庄子对于生死问题,在理念上有清楚的认识。不过,观念与实践毕竟是两回事,多少人想得到,做不到。庄子“鼓盆而歌”,可以算是生活中的一次实践。然而,关涉别人(即使这人是与自己生活半生的太太)与关涉自己毕竟还是不同,多少人是旁观时清,当局时迷。
庄子面对自己的最后归宿,表现出来的忠于自己理念的清醒态度,真正让人信服。他拒绝了弟子们要厚葬他的计划,说出上面这番于他极自然,于别人却惊心的话。随后的对答更坦白,也更惊心动魄。弟子说:这样的话,我们怕乌鸦、老鹰来吃您啊。庄子答:地上为乌鸦、老鹰吃,地下被蝼蛄、蚂蚁啃,夺那边的食物给这边,多么偏心啊!(弟子曰:“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。”庄子曰:“在上为鸟鸢食,在下为蝼蚁食,夺彼与此,何其偏也!”)
庄子的态度出乎常情,但这确实是彻底实践其生死观念的自然结果。况且,从实际的经验来看,庄子也是聪明的。厚葬没有好结果,历来多有论者。《吕氏春秋》有《安死》一篇,说如果在石上铭刻,昭告世人这下面有许多珍宝,一定会被人笑话,而厚葬与此不是一回事吗?(“自古及今,未有不亡之国也;无不亡之国者,是无不抇之墓也。”)那么薄葬如何呢?宋代张耆和晏殊遗言不同,张厚葬而晏薄葬。后来盗墓贼在张墓中所获甚多,还没迫近棺椁,已经拿不下了,于是退走;晏殊墓中只有瓦器数十具,盗贼花了大气力,却得不偿劳,恼羞成怒,用斧头敲碎了这位大词人的遗骨。(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)
厚葬不行,薄葬也有此不虞之祸,那还不如就不葬!
另外附上同期适合小朋友的一本‘庄子’的书,其实它是一套中的‘庄子’。
‘国学典籍那么好看’之‘《庄子》有哲思’,孟琢。(可惜国学两个字在现阶段已经被污染了…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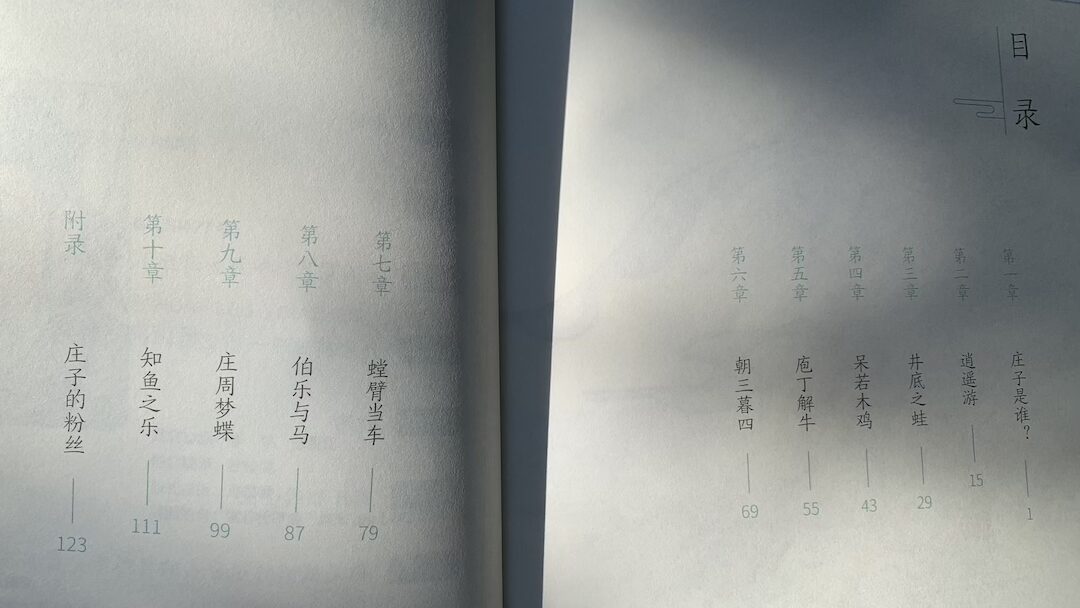
<完>